来源:游戏研究社
本文作者SulfuriumUranide,有机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现任国际顶级化学期刊《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执行编辑,曾在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先后担任《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和《自然·化学(Nature Chemistry)》等知名期刊学术编辑。
SulfuriumUranide曾为我们带来一些有趣的跨界科普:《为了讲故事,人类到底虚构了多少化学元素?》《两枚塑料蛋蛋,正在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次则讲述的是严肃科学界中经久不衰的……烂梗讨论。
1968年,荷兰计算机科学家Edsger Dijkstra在《计算机协会通讯CACM》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头就对编程语言中常见的goto语句大加挞伐:“多年来我一直注意到一个规律:程序员的水平跟他们代码里用goto语句的密度成反比……我深信,所有‘高级’编程语言都必须废除goto语句”。
那么,什么是 goto 语句?它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 go 和 to,顾名思义就是“跳转”。简单来说,这是一种直接从程序代码的某一部分跳到另一部分的指令,就像一个不打招呼的“传送门”。
初看起来它似乎很方便,但风险在于会打乱程序的逻辑结构,让代码变得像程序员自己都可能迷失其中的一团乱麻。

从外行角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你正在玩《黑神话:悟空》,突然跳出了一个传送门,把你带回了86版《西游记》的某个片段,那种“错位感”和混乱就是 goto 滥用带来的潜在后果。
Dijkstra投稿时的标题原本平平无奇——《一个反对 goto 语句的理由》(A Case Against the Goto Statement)。
但时任《计算机协会通讯CACM》 编辑 Niklaus Wirth 大概嫌这标题“没有传播力”,大笔一挥改成了“中二感爆棚”的《goto 语句有害》(Go To Statement Considered Harmful)。
这就好比今天某条微博突然爆出惊悚标题“某编程语法有毒!”,任谁看了都得点进去一探究竟,直接把话题热度拉满。连大神高德纳Donald Knuth读到后都不禁玩了个谐音梗,打趣道:“後藤博士(Dr. Goto,指日本计算机科学家後藤英一Eiichi Goto)脸上笑嘻嘻地抱怨说自己总是被‘消灭’掉。”

瑞士计算机科学家Wirth(左)是包括Pascal在内的多种编程语言的主设计师,因此获1984年图灵奖,曾在1995年提出吐槽软件愈发臃肿的Wirth定律,即软件变慢的速度永远超过硬件变快的速度。
高德纳(右)的鸿篇巨制《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向来被认为编程界的“圣经”,他也是1974年的图灵奖得主
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Wirth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就好像执行了一条后果不明的goto语句,一下子带火了X cosidered harmful这个大众媒体中“吸睛”效果满满却早已不新鲜的烂梗,带癫了计算机学术界。
随后各种“有害论”的文章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在谷歌学术上以considered harmful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有六万多条。
其中就有一些放在今天看来让人莞尔的观点。比如“人工智能之父”、1971 年图灵奖得主 John McCarthy 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对电子邮件有害》。

这篇文章的观点,听起来像今天有人说“手机对短信有害”,但别忘了,这可是互联网还没普及年代的严肃发言!
真正把X considered harmful梗推向高潮的,是围绕 Dijkstra 原文的一场“编程界内卷”——以“结构化编程”之争为主题的多轮论战。
时间一晃过了小二十年,1987年3月Frank Rubin发表了篇怒斥《goto有害论》的反击文章,标题叫《“goto有害论”才有害》。一石激起千层浪,俩月之后CACM集中刊发了一系列题为 《‘“goto有害论”才有害’到底害不害?》的讨论,汇集了正反双方多家观点。
 可见擅长多层嵌套的编程大神们玩起套娃梗乐此不疲,丝毫不输任何一场热门弹幕大战。
可见擅长多层嵌套的编程大神们玩起套娃梗乐此不疲,丝毫不输任何一场热门弹幕大战。不过作者本就是这样的,编辑只需要考虑吸引眼球就可以了,可是作者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这下论战的大男主Dijkstra坐不住了,非常不爽地以题为《记一次令人失望的笔谈》的战斗檄文直接开喷。开篇就大加抱怨“以为你们多少有些长进能替我分忧,没想到我还是独孤求败”,到了结尾仍旧怒气未消“都过了二十年你们还是幼儿园撒尿和泥的拉胯水平,搁那玩呢?!”

这场论战影响深远,ACM从此禁止了主观意味如此浓厚的讨论,但也进一步把X considered harmful推向了潮流前沿。以至于又过了十几年有人忍无可忍呼吁《‘有害论’文章实在有害》,连自相矛盾都顾不上了
Dijkstra的风格一贯犀利,而他1972年图灵奖演讲的题目却是《谦逊的程序员》(The Humble Programmer),强调要充分认识到编程的巨大难度,以非常谦卑的态度去完成任务,才能大幅提升自己的姿势水平。令Dijkstra始料不及的是,“有害论”的回旋镖随即射向自己,同年年底就有人发表了题为《傲慢的程序员:Dijkstra与Wegner之流贻害无穷》的文章,把Dijkstra等的学术观点批判一番。

个性鲜明的Dijkstra极其讨厌使用电脑,却偏爱万宝龙“大师杰作”系列钢笔用于写作,曾宣称: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个计算机科学家就要在电脑上浪费时间,就好比医学专家不能以身试病
类似X cosidered harmful这种万能短语模板,其实早就活跃在人类语言中。但直到 2004 年,语言学家 Geoffrey K. Pullum 才正式给它取了个名字——雪克隆(snowclone)。这个名字灵感中还隐藏了一个刨冰筒(snow cone)的双关谐音梗:冰是一样的冰,靠不同口味糖浆才分得清,和这些“万精油句式”可以随意替换关键词的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雪克隆一词来源于一个流传甚广的雪克隆本身——如果爱斯基摩人有N个关于雪的单词,那么X有Y个关于Z的单词
在传统纸媒年代就不罕见的雪克隆,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迅速得到了普及,很多则历久弥新。来源于五十年前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雪克隆XX门,至今连中文媒体都还常常用来报道带有负面甚至丑闻色彩的新闻。

出处已不可考的粉色是新黑色Pink is the new black也被Netflix雪克隆成自家剧名《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
通过卫星直播的“沙漠风暴行动”不仅让世人见识了现代战争的威力,更是在西方世界带火了XX之母(The mother of all X)这个来自阿拉伯语的雪克隆,甚至被美国方言学会选定为1991年的年度热词。一切只因“带火主播”萨达姆在警告多国部队时夸下的海口:“让所有人都明白,这场战斗将成为所有战斗之母”。

多年后美国空军开发了GBU-43/B大型空爆炸弹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 bomb还不忘恶趣味地callback一下萨达姆,取了个缩写相同的绰号炸弹之母Mother Of All Bombs。
而军备竞赛中从不甘落后的战斗民族开发出威力更大的空投高功率真空炸弹时,针锋相对地命名为炸弹之父Father of All Bombs,仿佛在洋洋得意地炫耀:“这是我的反制措施Counter Neutralization Measures”
当大众造梗变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之后,科学家们也不甘寂寞。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条历史悠久、老少咸宜的雪克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因17世纪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而闻名,但有研究表明To X or not to X早在这部剧作问世前就出现了,原来浓眉大眼的莎翁也是玩梗高手啊!

某学术期刊目录导语就曾尤其钟爱这条雪克隆。比如讨论电子到底是不是在硼原子上,那问一下to B or not to B(硼元素符号是B)没毛病吧?
而当四面体的白磷分子P4能被拆开稳定存在时,总得好奇是不是两个磷原子Two P or not two P?
后者还隐藏了个谐音梗,磷元素符号P和单词pee(撒尿)同音,磷元素恰好最早就是从尿液中提取的。但这个问题可没法思考太久,不然容易憋坏了
雪克隆和梗(meme)以及套话(cliché)密切相关,《洛杉矶时报》记者David Sarno认为雪克隆就是被“梗化”的套话(memeché),把关键词挖掉,人们就像玩填词游戏一样拼出各自的版本,自带一种“全民创作”的游戏精神。这就成了预制菜一样的“预制语言”,如果说“二创”短视频是快餐式二创,那么雪克隆就是瓜子、零食式二创了,张口就来,欢快地活跃在弹幕、评论区之中。

当然了,经常创作雪克隆的朋友都知道,玩梗容易热评难。这条雪克隆的原句是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杀人容易抛尸难,最早可能来自《中国刑侦大案》这部纪录片
电影《我的1919》中陈道明饰演的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慷慨陈词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也成了爆款雪克隆,网友们纷纷把自己竭力维护、自认意义重大的事物通过“耶路撒冷”具象化了。

其中耳熟能详的一定少不了:3D区不能没有蒂法,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在调侃“散装江苏”和“徽京”热潮中,“耶路撒冷”雪克隆在形式和意义上又得到了升华:南京是江苏的萨拉热窝,安徽的柯尼斯堡,台湾的耶路撒冷,板鸭的……
至于本文作者的几次投稿,多少都是带些“跨界”属性,因此每篇评论区中都不乏在油盐社,你甚至可以看到/研究oo这样的感叹,相信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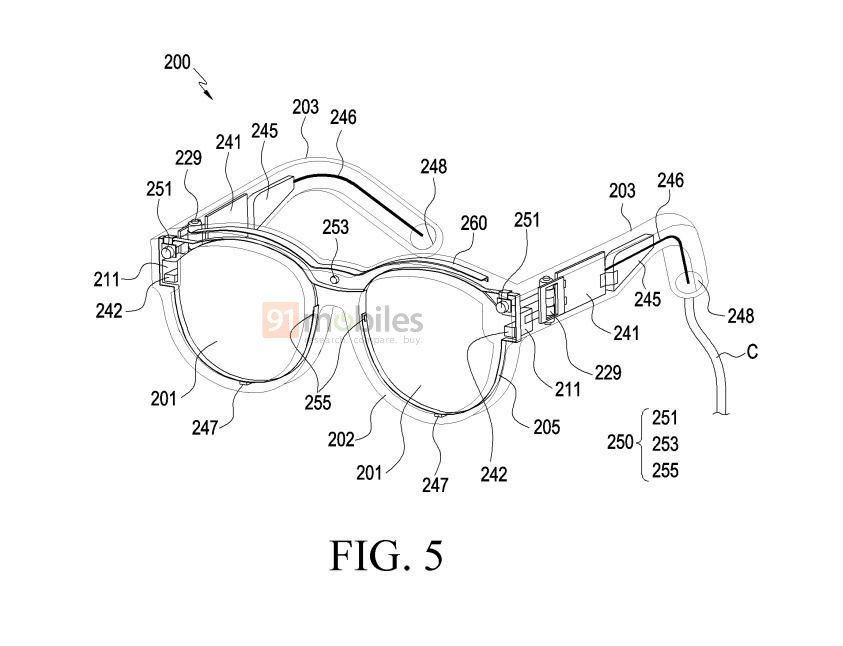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