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狮少年2》的上映,可谓国产电影在今年岁末的一大惊喜。
近些年来,“国漫崛起”的呼声不绝于耳。乘着二次元文化与产业的东风,创作者们纷纷到神话传说中寻珍觅宝。一时间,神怪奇幻纷至沓来。2021年,《雄狮少年》的出现,将国产动画电影从神话的云端带回现实的地面。三年后的续作,在动画技术与叙事手法上更为成熟。热血的青春故事被镶嵌进更为宏大的文化框架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意涵。
从舞狮到格斗暗喻从传统到现代
《雄狮少年》里,留守少年阿娟在同名女孩阿娟的启蒙下,投身舞狮比赛,完成了从“病猫”到“雄狮”的蜕变。这部散发着浓郁岭南烟火气息的电影,采取了近年来神话题材动画的常见套路:镜像结构与变身仪式。少男阿娟/少女阿娟的人物组合,与病猫/雄狮的身体修辞,指向的是精神分析意义上主体性的构建。戴上狮头朝天一跃的时刻,是英雄变格,也是自我确证。显然,与同时期的许多国漫作品类似,《雄狮少年》也关乎现代意义上自我价值的追寻。
在第一部的后半段,去城里务工的父亲重伤归乡,为了赚钱养家,年纪尚小的阿娟也只能进城打工。《雄狮少年2》延续了这一情节,不过将叙事时空变换为更加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上海。然而,建筑工地的安保工作无故被辞,前来投奔的朋友阿猫、阿狗也无处容身。影片以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乡下人进城”叙事,让岭南小子阿娟直面一个更加繁华也更加陌生的现代世界。面对个人与家庭的双重困境,他只能投身格斗比赛,以求绝处逢生。
表面上看,《雄狮少年2》依旧讲述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成长故事。影片甚至采取了与前作如出一辙的叙事结构:都是通过拜师、训练、比赛的模式来完成人物的成长弧线,当然类型化叙事变得更加娴熟。但显然,《雄狮少年2》“打怪升级”的难度大为增加,现实意味也更为强烈。更本质的变化在于,影片让来自乡土世界/熟人社会的个体加入现代世界/法理社会的生存法则。
舞狮与格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依赖多人协作的象征仪式,而后者是讲求单打独斗的实用技术。从舞狮到格斗的变化,意味着要袒露身体,直面对手,迎接痛击。这是少年阿娟新的命运:栖身芜杂的野草,去对抗现代丛林的法则。
二次元小叙事跨越圈层展现共同价值
舞狮遭遇格斗,意味着传统遭遇现代。显然,影片相较前作的另一重要变化,在于将舞狮/武术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嵌入更为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中。
这种现代性反思的叙事虽然并不新鲜,但可贵的是完成度高,叙事流畅且情感充沛。从类型上看,影片也明显延续了《精武英雄》《霍元甲》《叶问》等功夫片的创作传统。功夫片自发轫之初,便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身体强健与民族自强的结合根深蒂固。《雄狮少年2》的开头有这样一幕:武师张瓦特为了拳馆生计,摆下擂台拳打各国选手,不料却被格斗高手肖张扬当场拆穿打假拳,只能落荒而逃。这是影片颇为有趣的一点:从拆解功夫神话开始,进而为传统武术正名,重新构建了一则全球化时代的新功夫神话。
当然,影片并没有秉持一种对立思维去看待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而是不断地借助片中人物之口去展现一种辩证的姿态:传统不仅要继承,更要兼收并蓄,推陈创新。近些年来,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备受瞩目。从传统文化的“两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命题的提出,都在不断强化着新的全球化语境中构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
就此而言,《雄狮少年2》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了二次元文化、现实题材与民族叙事的耦合。日本学者东浩纪对于二次元文化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当代御宅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消费由各类萌要素组成的庞大“数据库”,通过其中各类萌要素的提取与组合来生成故事,这是一种新的故事模式。
在今天,以二次元为代表的不同趣缘群体分享着各自的小叙事。这些小叙事如何通向一种跨越圈层的普遍情感与共同价值,是今天的文化生产面临的难题。
在此之前,同为现实题材、洋溢着二次元风格的电影《闪光少女》给出了一种示范。影片以民乐与西乐的对决,结成了“传统文化”与“二次元”的战略同盟关系。沿着《闪光少女》的足迹,《雄狮少年2》在熟练使用“萌”要素和“燃”叙事等更符合年轻群体趣味的语法的同时,将青春成长与家国认同紧密交织,融合了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
为现实问题提供想象性纾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雄狮少年2》不仅老少咸宜,更重要的是中西、新旧融通。它熟练地使用好莱坞式的类型法则与动画技术,展现中国现实问题,去讲中国故事。
不过,影片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想象与书写或许需要进一步深思。将两部影片合起来看,它们讲述的实际上是两代新工人的困境:阿娟父母在城市中无法获得应有保障,在乡村还有子女留守问题;新一代农民工子承父命,在大都市里同样难找立锥之地。新工人群体的困境,本质上是城与乡的结构性问题。《雄狮少年2》的解决方式,是巧妙地将新工人群体面临的难题转移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于是传统文化的胜利,也就意味着这一群体的生存问题得到了纾解。
这种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也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处理上。第一部中,男女阿娟之间尚且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第二部里,阿娟与拳馆继承者小雨似乎缔结了跨越身份的情谊。影片末尾,阿娟向小雨发出了“拳馆还在,家还在”的信息,召唤海外游子归来。由此,阿娟作为新工人群体的代表,从第一部中被启蒙的对象,化身为第二部里的拯救者。武术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让异乡人阿娟在城市里安身立命,也让不同的社会群体找到共同的原乡。
有趣的是,在2024年末,《雄狮少年2》与稍早上映的《好东西》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上海都市景观。前者聚焦新工人群体,以男性视角和燃向叙事塑造男性气质;后者聚焦新中高收入群体,以女性视角与谐谑叙事拆解父权秩序。两种互为镜像的表述,构成了当下中国多元而有趣的文化景观。
当然,影片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想象和对现实问题的纾解,仍然存有虚妄的部分。对于创作者而言,或许也只能透过这种方式去化解。就像我们在这段一二十年前的旧时空里,看到的正是当下人们所遭遇的生存问题、媒介暴力与集体情绪。
而无论是对于新工人群体还是正面临人生难题的你我而言,影片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可能和慰藉。或许,在人生前路不明时,不妨再高诵李白的那一句: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文/李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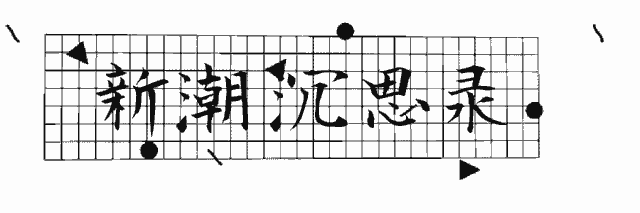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